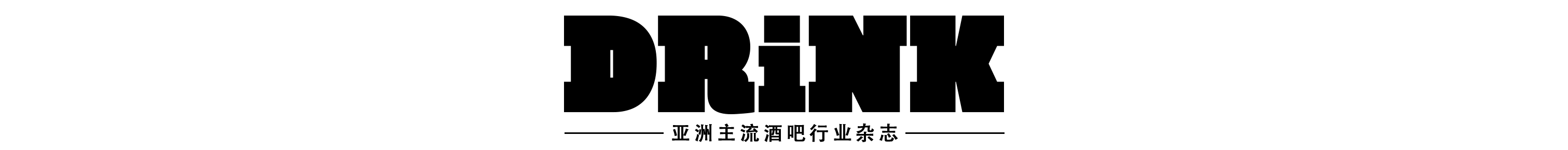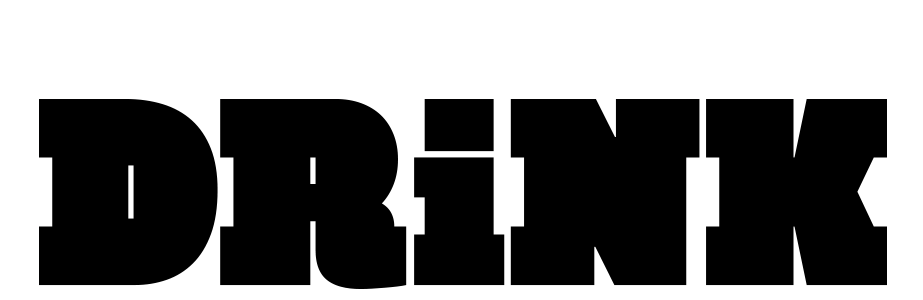王玉文坦述自己在酒吧里当“牧师”的骄傲心声以及开拓中国二线城市市场的历程。杨耀东采访整理。
我高中的时候曾爱上一个女孩。我想在她面前秀一把,所以我看了一个演示如何调制血腥玛丽的视频,我觉得调酒师很酷。我父亲当时出差,家里留了一瓶上好的蒙古伏特加。我把它跟番茄汁和辣椒仔调在了一起。那时我没有伍斯特沙司,所以我买了一些醋来代替。女孩说它尝起来还不错,但现在想起来,它一定很难喝!
我老家在安徽。我高中的时候学了美术,艺考生进的大学,但一年后我退学了。那是2007年底的事情。之后,我去北京找了份调酒师的工作金并且爱上了这个职业。当时面试的时候,我跟老板夸口我会做多少鸡尾酒,我知道多少个配方。我自信满满。现在想想还是挺可笑的,因为当时我完全没有真正的鸡尾酒知识。
我工作的第一个酒吧叫No Name,它在北京后海,我在那里待了大概两年。那时候,这家酒吧很火。生意特别好,没有提前预订都不让进。李亚鹏和王菲都经常光顾。气氛是很热闹的,不过酒水一般。我们只提供一些常见的鸡尾酒,比如说莫吉托和长岛冰茶。
起先,我的家人并不介意我做调酒师。趁着年轻玩几年对他们来讲是可以接受的。但他们希望我能很快回家找一份正经的工作。在他们眼里,调酒不能算是一份职业。离开No Name之后,我去了一家名叫亿多瑞站的美式餐吧。它的薪水很高,但我还是辞职了,因为我想跟随我的日本老师大西代祐,在他跟内山基成合开的暮光酒吧工作。在看过大西先生调酒之后,我意识到自己对鸡尾酒其实根本不了解。于是我在暮光工作了大约两年半。但实际上,大西先生教给我最多的不是如何调制鸡尾酒,而是如何面对客人以及一些细节方面。我耳濡目染了他的谨慎、对细节的注重和敏锐的味觉,他还教我如何确保客人喜欢那些鸡尾酒。

我在2012年去了天津。那之前我碰到了很多想和我合作开酒吧的投资人,但陈世能打动了我。他对鸡尾酒和威士忌感兴趣,所以我们有很多共同点,而且他对在二线城市普及鸡尾酒很有一套。因为他,我离开北京去了天津的普蔻酒吧。当时,天津的鸡尾酒界好似一片荒漠。虽然也有小酒馆,但几乎没有卖真正的鸡尾酒的。普蔻是唯一一家专门经营威士忌和专业鸡尾酒的酒吧。
陈世能就像一个老大哥,他教我如何做生意。刚开始为他工作的时候,我想把鸡尾酒发挥到极致,让客人来喜欢。但那时候的客人并不愿意为那种鸡尾酒买单。然而,我们同时又想让我们的酒吧有品质。所以陈世能的策略是坚持做花哨的鸡尾酒来吸引客人,培养出忠诚度之后再把好的东西介绍给他们。
普蔻的房子原是医院的锅炉房。天花板最高有九米金很有哥特式的风格。它在市中心,但我们并没有挂出明显的标识告诉别人我们在哪儿,而且正面还有一个大铁门。那些第一次来这儿的人很难找对地方,但经常是老客人带新客人。这家店的生意目前非常好:一周有三到四天,客人需要等位。
“我觉得自己是个牧师:吧台就是布道台,酒客就是信徒”
2014年5月,一个朋友带我们去昆明考察市场。我们想在那里也开一家普蔻。我们是在2014年8月开始筹备的,去年3月开始试营业。酒吧所在的基督教青年会1933之前是个教堂。它是美国飞虎队当年居住的地方,并且是30年代云南最高的建筑。把墙纸剥掉是件让人伤心的事情,但我们保留了复古的风格,不过和一些现代的东西结合在了一起。
昆明不是一座大城市,但这里有很多酒吧、酒馆和夜店金数量是天津的五倍甚至八倍。有几家大学甚至邀请我去上鸡尾酒课。云南和中国别的地方不一样:学校看重的是餐饮知识和能帮你找到工作的实用性技能。班先海现如今是云南财经大学的老师,他之前是做花式出身的。而昆明学院旅游学院的田芙蓉之前也是一名调酒师。他们积极地推广和传播鸡尾酒文化。我想父母也会鼓励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更好地享受生活金比如懂得不同类型的咖啡、会调鸡尾酒。
明年,陈世能和我可能还会到像大连和青岛这样的城市去。鸡尾酒对我来讲是社交的工具。有时候你给某个人调一杯鸡尾酒,你也就交了个朋友。我有时候觉得自己是个牧师,特别是我们酒吧开在曾经的教堂里,就更顺理成章了:吧台就是布道台,客人就是信徒。
普蔻酒廊,昆明五华区鼎新街4号青年会1933原址,0871 6823 7731
天津和平区承德道与山东路交口,022 2711 9858
本文刊登于《饮迷》第4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