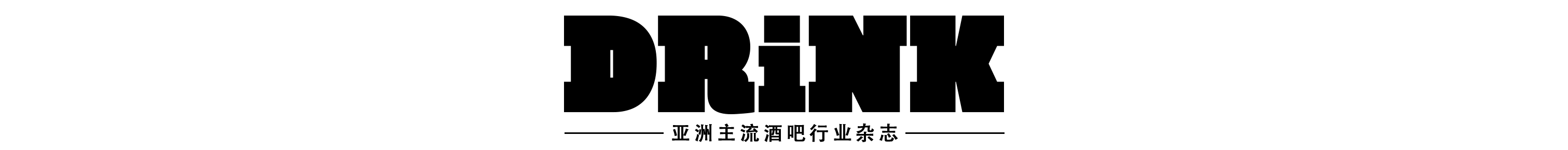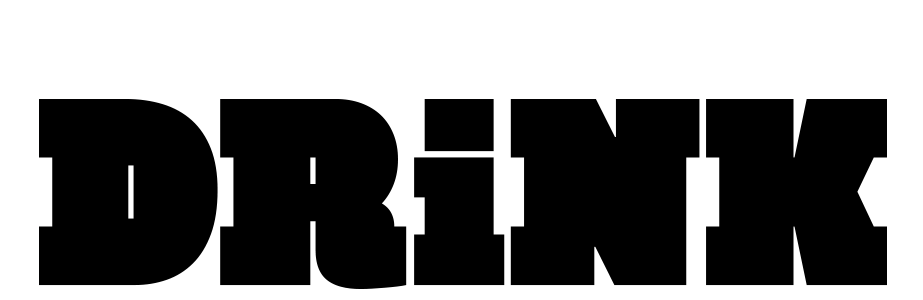Unlisted Collection董事长卢立平在全球五个城市成功打造了一系列精品酒店和知名餐厅,包括新加坡、上海和香港。而这一切都始于他对老建筑的热爱。Dan Bignold撰文。
“我感觉像是一个自然资源保护论者,”卢立平说,“我在挽救老建筑时总有种骄傲感,比如我们在新加坡做的1929酒店,或是开在伦敦贝思纳尔格林的市政厅酒店。”卢立平是国际酒店餐饮集团Unlisted Collection的董事长,目前集团旗下拥有分布在五个国家的七家精品酒店、超过20家餐厅和两家单独运营的酒吧(新加坡The Library和Longplay)。他对旧日事物的痴迷不仅止于建筑。除了20世纪中期的家具,他还收集老珐琅广告牌和古董理发、验光及牙科座椅。“我还喜欢老电扇、通用电气风扇和100年前英国人爱用的网罩风扇。我喜欢机械的东西,”他说,“这些摇头风扇不能放在我的酒店里,因为它们不是太脆弱就是太危险。其中许多都产自电气化时代早期,有着开放线圈和大大的铜叶片,足以把你的手指切断。动力太大。一点都不安全。”
卢立平是新加坡人,但他认为自己对传统的兴趣源于在爱尔兰度过的童年。他的父母都是医生,当时在都柏林教书,他于1972年在那里出世。后来他回到了新加坡,但在12岁那年重返爱尔兰入读寄宿学校。“我认为它是我生命中个性形成的一个时期,而且让我拥有了不同的视角。那时我经常旅行。如果去伦敦,你会看到许多漂亮的老建筑,它们都被保护得很好。所以我一直觉得老房子值得保留下来。”他把1990年代的新加坡拿来作对比,那时大多数不动产业主都把历史保护建筑(及其日常维护)看作是一种累赘,而不是优点。“那时人们对历史保护建筑并不了解。如果了解的话,他们就会避开它们——没人希望市区重建局找自己的麻烦。在那个时期,人们肯定要把房子建得大十倍,这样价值也会高十倍。没人把那些老建筑看作真正的资产类别。”
除了卢立平。他回到新加坡,在1990年代后期从事律师工作,办理破产业务并看过大量廉价急售房产的抵押文件。“我注意到了那些很有意思的房产——全都是店屋。我在国外生活了许多年,很喜欢牛车水的这一点。它反映了新加坡的独特之处。所有这些新的高楼,你可以把它们建在香港、伦敦——它们看上去都一样。但店屋只有在亚洲这个地区才能看到——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的小块地方。”他注意到恭锡街50号的房子已经拍卖了三四次,但一直没有买主。那时的恭锡街和今天很不一样。“现在只剩下两家妓院,但我们把房子买下来的时候80%是红灯区。”在父母的帮助下,他决定把这栋房子买下——“价格非常便宜堂并在两年的整修后开出了首家餐厅Ember(位于底楼)。在接下来的2003年,拥有32间客房的1929酒店开业。

许多大型国际酒店集团都是和开发商签订租约、仅负责经营管理,但卢立平在寻找房地产机遇——这反映了集团的地产所有权模式。“酒店本身的盈利不是最终目标,”他解释道,“我们希望获得良好的资产收益,再把它们投入到其他项目中去。”这一模式在2013年便起到了作用:卢立平将恭锡街的酒店出售之后回租。这就是他的逆势策略:“我们的惯例是寻找地段略为偏僻、但仍然相对中心的房产,这样我们总能用更好的价格把它买下来。不管在世界上的哪个大城市,你总能找到那样的小块区域,它们还没有中产阶级化、没有转型,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它们都还有点不时尚。”那么,他会觉得是自己造成了接下来的转型吗?尤其考虑到1929酒店开业后的十年间,恭锡街显示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我们赶上了第一波浪潮,没错,人们会问我是不是预见或造成了这一切。但答案是否定的——让这些街区改变的力量比任何个人都要强大。我们只是碰巧在正确的时间身处正确的地点。”
然而,这正是为什么他对历史传承的热情看起来像商业上的精明。卢立平喜欢投资“引人注目、有特色的建筑”,因为这些房产在一个区域的繁荣发展中受益最多。的确,他坚称实实在在的建筑总是占据着集团战略思考的第一位,这对一位21世纪的国际酒店经营者来说非同寻常。“最重要的永远不是城市。你必须爱上一座建筑。我们发现了悉尼老旧的卡尔顿联合啤酒厂——后来它变成了2015年开业的老克莱尔酒店——它令人难以抗拒。但我那时已经大约五年没去过悉尼了。它不在我的关注范围内。”他表示,接下来就是迅速对每个目的地做一些研究,以确保“我们不会踏上一个巨型地雷”,然后将房产买下。集团最近在都柏林的收购正是如此:坐落于南弗雷德里克街、横跨三栋乔治王朝时期联排房屋、拥有26间客房的圣三一酒店,距离他父亲曾经执教的圣三一学院仅有五分钟路程。
早在2000年,当集团购入第一处房产时,卢立平并没有酒店餐饮业方面的培训。“坦白说,我最开始对酒店毫无兴趣。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直到我买下了1929。”但他并未因此而不知所措。他在工作中学习(“开酒店不是造火箭——尽管酒店经营者可能会有不同的说法——但许多事情都要靠直觉”),并聘请了真正的专业人士,这一做法也成为了集团以主厨为核心的餐厅运营路线的基石,包括江振诚(Restaurant Andre)、David Pynt(Burnt Ends)以及众所周知的与Jason Atherton的多次合作。卢立平坦承,他直到今天都没学会怎么做厨房排班表,“但我不是运营餐厅的那个人——在这方面我依靠他们。”的确,他避免进行微观管理,让主厨和酒店经理在工作中拥有权力和自主性,从而把他们的个性注入到门店中。“我们公司的角色是做那些他们不感兴趣或不擅长的事——财务、人事——会让他们分心的事。我们来看数字、分析费用比和损益,门店报告客人投诉的次数。有时,我几个星期都不会到店里。我可能是世界上最放任自流的经营者之一。”
通过与Atherton的合作,他在亚洲开创了严肃美食加轻松氛围的模式,正好契合集团以生活方式为主导、刻意不走奢华风的路线。两人的合作在新加坡已经结束,但其他项目包括悉尼的Kensington Street Social、香港的Ham & Sherry、22 Ships和Aberdeen Street Social、以及上海的Commune Street Social。“从战略上来说,它不再合适了。我们覆盖了这么大的地理范围,没必要把新加坡包括在内。它变得太难管理了。”他对自己的三大亚洲运营中心进行了比较,认为新加坡和香港可以接受更复杂的餐厅概念——但即便如此,风险仍然存在:“Burnt Ends刚开的时候——明火直接烹饪——评论家都很困惑,‘为什么这些菜都烧焦了?掠相反,香港和上海更像是“派对之城”:“在新加坡,人们依然大部分时间都在家里做饭。在香港,人们几乎从不这么做。”

于是,我们又回到了收藏品的话题——这次是1929酒店大堂里放着的一张有80年历史的理发椅。“这样的东西可以放在酒店里。它们实际上很难坏掉——大量铸铁、过度设计、像头野兽,”他说,“它从一开始就摆在这间大堂里。孩子们爬上爬下,液压泵仍然有用,在我死后它还会继续存在很长时间。现在没人能设计出这样的椅子了。”
1929酒店,新加坡恭锡街50号
本文刊登于《饮迷》第4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