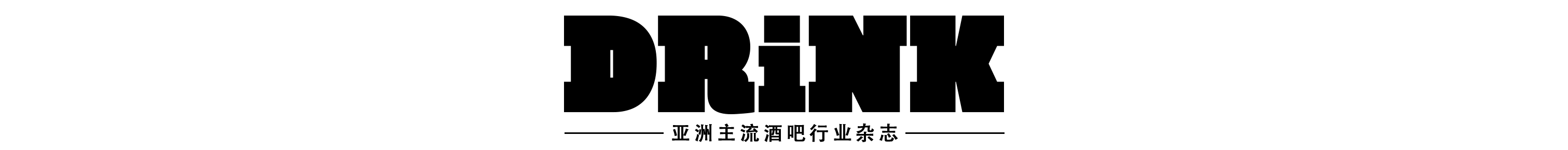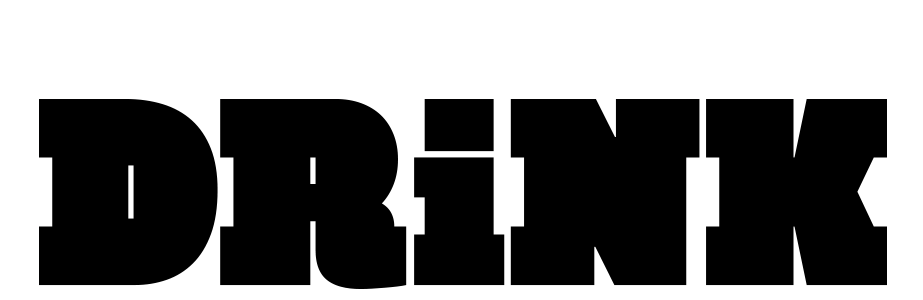墨西哥公主?羽毛饰物?非也非也。关于鸡尾酒的早期历史,我们还有一种更加可信的说法,来自David Wondrich。
到底是谁调制了第一杯鸡尾酒?这位他或者她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完成了这一壮举?这历史性的一刻到底又是在什么时间降临的?这些问题,我们怕是永远也无从解答了。历史几乎从不关注生活中真正重要的事情,倒是总喜欢跟什么战争、瘟疫一类大煞风景又昙花一现的东西搅在一起。其结果就是,如今坊间流传一大堆号称鸡尾酒这一至尊饮品之起源的神话传说或者酒吧故事,而又无一具备现实佐证。所以说,我们还是先把这些天方夜谭撇开不谈吧,来看看我们手头真正掌握的实证材料。
所有牵涉到名为“鸡尾酒”之饮品的最早期文献无一例外都出自美国东北部,奥尔巴尼州、纽约州、波士顿以及纽约城之间的一个三角地带。这个词最早以铅字形式出现是在1803年,在新汉普郡阿默斯特市的《Farmer’s Cabinet》上。那位醉熏熏的作者在文中说道:“喝下一杯鸡尾酒”乃是“提神醒脑的佳法”。然而很不幸,《Farmer’s Cabinet》并没有告诉我们这种鸡尾酒到底是什么成分。直到三年后,纽约州哈德逊镇(地理位置介于纽约城与奥尔巴尼州之间)的一份报纸才首次给出了此种饮品的定义:“这是一种令人兴奋的酒饮,由各种口味的酒与糖、水、苦精混合而成。”到了1815年,纽约城内开始饮用鸡尾酒(通常在早晨),也正是从这座城市开始,鸡尾酒传遍了整个国家—到了1830年,在美国的任何地方你都能找到鸡尾酒了—继而整个世界。
起初,就大多数人所喜欢的鸡尾酒而言,其配方正如上所述;而其中所选用的配酒,通常都是金酒或白兰地;到了19世纪中叶,美国威士忌才逐渐取代了这两种酒的地位。19世纪40年代,原始的鸡尾酒终于吸收了后来成为其核心成分的一大元素:调酒师们开始以冰块代替水来进行调制。这种至关重要的改良之后,鸡尾酒的基本成分就稳定下来,我们通常所做,只是往其中再增减一点利口酒、苦艾酒或者味美思而已。直到20世纪初,由于布朗克斯鸡尾酒(金酒、橙汁、味美思的混合)开始流行,鸡尾酒的配方里才加入了橙汁,排除了苦精。
“我们只能倾向于相信最无碍于常识的那些解释”
至于“鸡尾”之名的源起,实在莫衷一是,这么多年下来,高头大论至少已有一打,但大多荒唐透顶,且没有一种具备真凭实据。在没有什么实实在在的文献材料表明此种饮料的确得名于某位墨西哥公主、某种法国蛋杯、某种饲养斗鸡的麦芽酒、某种羽毛饰物或者任何其它奇谈怪论之前,我们只能倾向于相信最无碍于常识的那些解释。
这一类共有两种,其一说之所以“鸡尾”命名此种饮品,是因为它能让你的“鸡尾”于清晨挺立——这当然是隐喻的说法;而另一种则认为,所谓“鸡尾”,应该来自赛马界的一种行话(如果你也幸好跑马,那么你应该也会喜欢混合饮料的)。在鸡尾酒问世的时代,混血马也被叫做“鸡尾”马。你若生在当时,又正巧往你手中那杯金斯林酒——这是由金酒、糖加水调制的一种饮料——中再加上了一点苦精(那是另一种酒,在当时苦精通常是直接饮用的)——那么你打算怎么称呼这杯中物呢?不就这么简单吗!
鸡尾酒早期发展史上的几大里程碑
1712年伦敦的一位药剂师理 Richard Stoughton医生以他的“大瓶装长生液”取得了皇家专利,这是一种以酒精为基础并添加苦味药草的混合液体,在当时,它还有另两种众所周知的名号,“Stoughton’s drops”,“Stoughton’s bitters”(斯托顿苦精)。之后,一无名天才又产生了往这种液体中添加糖、水,以及金酒或白兰地的好主意,于是最早的鸡尾酒就由此诞生了。
1815年一个名叫 Willard的年轻人——无人知其姓氏——开始出没纽约的酒吧。没过多久,他就以“城市旅馆的威拉德”而名声远播。这就是美国的第一位著名调酒师。这位仁兄之所以能同时在当地人和旅行者中成就其声名,靠的就是他提供的宾治酒、冰镇薄荷酒,以及鸡尾酒。
1862年一位名叫 Jerry Thomas的年轻调酒师发表了《调酒师指南:绅士酒柜伴侣》,这就是世界上第一本调酒师指南。作为一名航海家、淘金者、戏剧赞助人、赌徒以及艺术家,Thomas曾花费十年时间周游美国,四处调制饮品并搜集配方。他的著作中包含的配方有近300种,其中有十种就是鸡尾酒的。
1884年马提尼酒配方首次付梓,见于纽约的几种调酒师指南。起初,它是英国金酒、味美思、苦精加上一点黑樱桃利口酒;到19世纪90年代,其成分又发生了重大变化,利口酒被去除,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原先采用的甜味美思被换成了干味美思。这番整备之后,这种饮料开始了它征服世界的征途。
1920年因为禁酒令,纽约著名的“荷兰旅馆酒吧”被迫关门,首席调酒师 Harry Craddock收拾起他的器具转投伦敦“萨沃伊旅馆”麾下。在成为萨伏伊首席调酒师之后,克拉德克也担负起了美式混合饮料推广大使之职,并把鸡尾酒的福音播洒到了整整一代欧洲酒吧客中。
本文刊登于《饮迷》第1期。